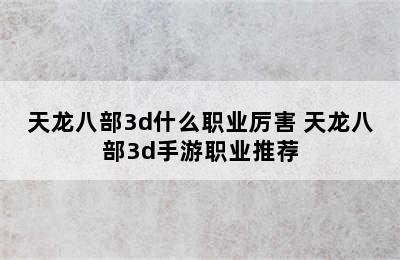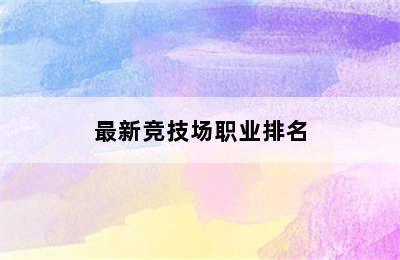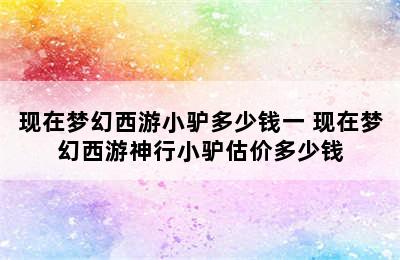1、最后一段: 于是论次其文。
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
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!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。
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
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戹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
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翻译: 于是我评论编次了这些文章。
经过了七年,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祸患,被拘禁在监牢之中。
于是喟然长叹道:“这是我的罪过啊!这是我的罪过啊!身体遭到摧残,再没有什么用处了!”我又转而深思:《诗》、《书》辞意隐曲,文字简约,是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考的。
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,于是演绎了《周易》;孔子被困于陈、蔡,于是写作了《春秋》;屈原被放逐,著述了《离骚》;左丘眼睛失明,才写了《国语》;孙膑被剔去膝盖骨,就研究兵法;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,世上流传他的《吕氏春秋》;韩非被关在秦国的牢里,著述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都是贤人圣人感情愤发而写作的。
这说明,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郁积,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,所以追记往事,思念未来。
于是我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猎获白麟的时候为止,叙述了陶唐以来的史事。
2、 《太史公自序》是《史记》的最后一篇,是《史记》的自序,也是司马迁的自传,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。
不仅一部《史记》总括于此,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。
文章气势浩瀚,宏伟深厚,是研究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的重要资料。
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: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,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;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,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《史记》的目的,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,以《史记》上续孔子的《春秋》,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、评价,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,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、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,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,忍辱负重,完成了《史记》这部巨著;第三部分是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。
全序规模宏大,文气深沉浩瀚,是《史记》全书的纲领。
全书纲领体例,《自序》交待得清清楚楚。
读者在读《史记》之前,须将《自序》篇熟读,深沉有得,然后可读各篇纪、传、世家;读纪、传、世家如果不得其解,仍须从《自序》中求得解答。
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《史记》的方法。
其体制如同《周易》的《系辞》,《毛诗》的《小序》,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。
清代牛运震曾评价:“《自序》高古庄重,其中精理微者,更奥衍宏深,一部《史记》精神命脉,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。
”(《史记评注》) 《史记》自《黄帝本纪》起一百三十篇,合起来说,是总的一篇。
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,承载得起,意理要包括得完,气象更要笼罩得住。
《史记》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,逐层卸下,中间载有六家、六经两论,气势已经极盛,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,行行列列,整整齐齐,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,可以说无往不收,无微不尽。
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,万壑朝宗,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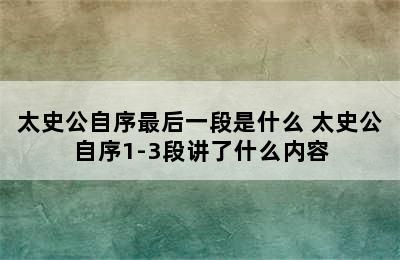
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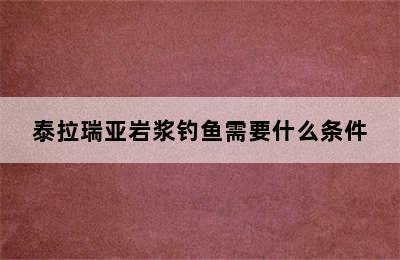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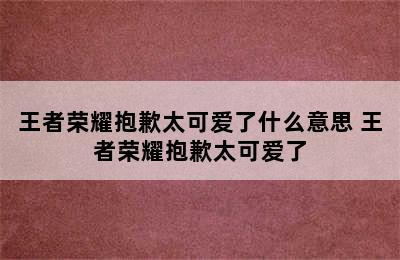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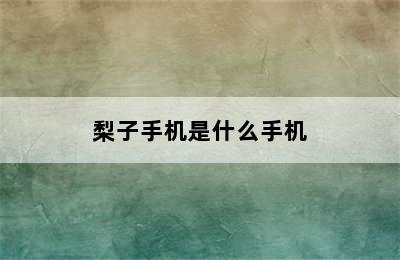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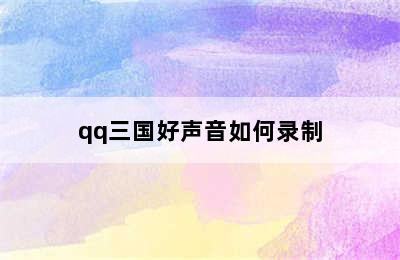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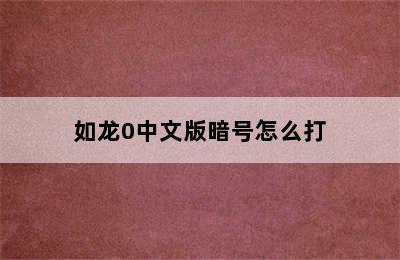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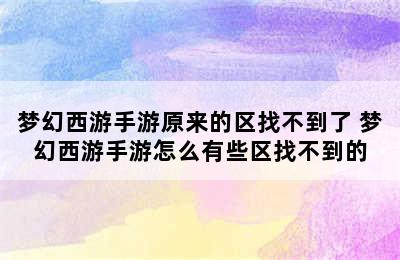
.jpg)